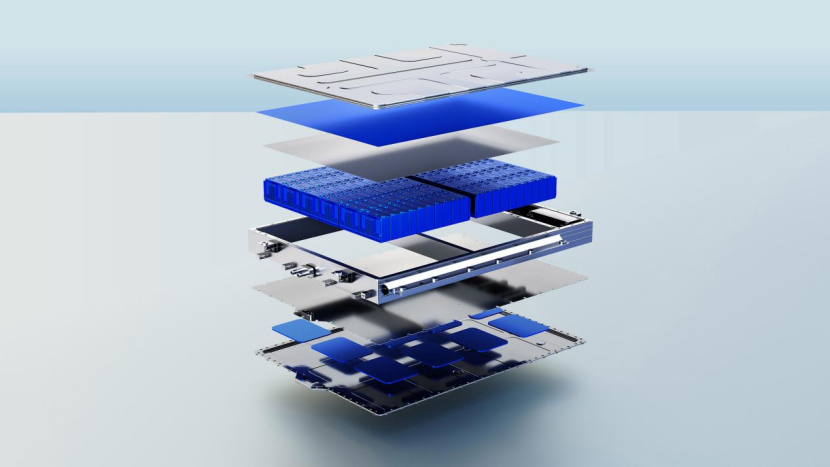文章目录[+]
“意造大观——宋代书法及影响特展”2023年秋在浙江美术馆开幕,立即成为杭城的一大热门文化事件。排着长长的队伍“蜗行”观展,我忽然发现,这里每一件展品的背后应该都有其创作、品鉴和流传等方面的精彩故事,然而却因为历史文献的稀缺、古今文化的差异、主观认知的局限,我们目力所及可能只看见了其表象,它的内涵、背景、身世、交集、命运等等更深层面的丰富信息,一时三刻恐怕是看不见的。
很想看见“意造大观”背后那些看不见的“大观”,于是我尽可能地开阔自己的眼界,努力钩沉、捕捉和再现那些仅存残纸片石、蛛丝马迹的历史真相,企望再有“大观”的看见,从而真切感知历史文化的意义。
《看见看不见的“宋四家”》第一篇我们见到的是为首的苏轼,这篇就接着看看黄庭坚吧——
利用计算机技术呈现的“黄庭坚像”
特别鸣谢:
灵隐管理处邵群女士
杭州孔庙方琦女士
王伟先生
晚清,杭州藏书家丁丙为护持运河两岸农田,主持疏浚湖墅塘河。某日,舟楫过半道红至牙湾(今霞湾巷)一带,忽见岸上田边一座祠庙,题额“苏家庙”。进内一看,主祀黄文节公(即黄庭坚,字鲁直,号山谷道人)。苏家庙祀奉黄庭坚,奇怪!
回家查阅藏书,见道光时杭人魏标《湖墅杂诗》有写苏家庙的纪事诗:
意思说,清湖三闸便利农桑,全靠当年苏东坡治理西湖时的付出,只是本地村民怎地数典忘祖,苏家庙却供奉起了黄庭坚?魏标也不理解苏家庙为何独祀黄庭坚。再翻雍乾时候杭州名士厉鹗的《樊榭山房集》,丁丙看见一则轶事:乾隆十七年(1752)厉先生去世后初葬西溪,但坟茔不久就荒芜了,于是有人就将他的牌位寄放于湖墅黄文节公祠。原来苏家庙就是黄文节公祠,丁丙也听说了这祠堂是当地苏姓人所建,黄庭坚又是苏门四学士之一,本来都是一家人,没啥好奇怪的。
可黄庭坚一生未到杭州,这祠庙又从何说起?不但丁丙,至今也无从所知。
民国十七年(1928)测绘《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》
确实,“宋四家”苏、黄、米、蔡,其中只有黄庭坚不曾到过杭州和两浙地区,他的文艺创作也殊少涉及浙江和杭州的物事,以至于前不久浙江美术馆“意造大观”特展在介绍“宋四家”与杭州的关系时,只提到了他的祖籍可追溯到唐代金华浦江。
然而讲书法,黄庭坚在杭州并非毫无“存在感”,相反,他的书法从南宋以至明清,一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杭州代代相传。
黄庭坚书法与杭州的关系,这故事还得先从这次“意造大观”展陈的他的《题浯溪大唐中兴颂摩崖碑后》说起——
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藏
北宋崇宁三年(1104)三月六日,湘江南岸的浯溪(今湖南祁阳)风雨如晦。在唐代元结撰文、颜真卿书丹的《大唐中兴颂》摩崖石刻前,一根藜杖扶持着伫立于此的黄庭坚。见到这篇颜真卿晚年成熟书法的典型作品,平素“极喜颜鲁公书”的黄庭坚顿时被那力能扛鼎、直透纸背的壮阔气势和浑厚韵味震到了,感动、痴迷、心醉、倾倒,苍老的身影竟然在刻石前徘徊三日,不离不舍。他在给书友的一首诗中说:“大字无过瘗鹤铭,晚有名崖颂中兴。”在这之前,他以为碑版大字莫过于镇江焦山的名刻《瘗鹤铭》,而今看见《大唐中兴颂》,这种横空出世的大唐气象,足以与“鹤”并驾齐驱。
故宫博物院藏
浯溪所在的永州,唐宋时期是流放罪臣的“传统”目的地。黄庭坚此时被朝廷打入“元祐党籍”,远谪宜州(今广西河池宜州),故而永州只是经过,还不是他这次贬谪的终点。面对一代忠臣国士的字迹,他“断崖苍藓对立久,冻雨为洗前朝悲”,饱含热情为《大唐中兴颂》赋写长诗(宣和二年[1120]被人刻在颜字右侧)。
这是黄庭坚逝世前一年的作品,通篇楷体大书,当是在颜体端楷面前的有意选择,却并非颜体的亦步亦趋,而是融通了具有他自己鲜明书风的行书笔意。
一吟堂藏
在永州,黄庭坚还到访了幽邃奇绝为永州之冠的淡山岩胜景,并留下了两首歌咏“永州淡岩天下稀”的诗歌。十二年后的徽宗政和六年(1116),淡山岩僧人智嵩将他这幅人书俱老的《题永州淡山岩诗》墨迹摹刻于岩壁上,由此而成为在此一百多处宋人题刻中名声最著的摩崖石刻。
岁月又过六百八十年,清嘉庆元年(1796)秋天,江苏无锡学者、书画家钱泳来到杭州。说起来,钱泳还是吴越王钱镠的三十世孙,袁枚《随园诗话》记载了他的两首《游西湖》诗:
“十年不识钱塘路,今到翻疑是梦中。峦翠难分南北寺,舟轻易扬往来风。数湾碧水通仙宅,一带苍烟没宋宫。何处吾家表忠观?几回搔首问渔翁。”
西湖山水他尤喜灵隐飞来峰,去年冬天还与“西泠八家”之一的钱塘黄易共游灵隐,并在飞来峰龙泓洞题名刻石。不到一年,他再游飞来峰。在龙泓洞一线天,他见这幽绝山岩嵌空如室,玲珑有致,忽然有悟,这不就是黄山谷《题永州淡山岩诗》所描写的景象吗?
钱泳书法以隶书见长,年轻时曾对黄庭坚书法下过功夫。他的金石学问又与众不同,属于兼善镌刻碑版的操刀手,常在石壁上自书自刻。今次他便摘取黄庭坚《题永州淡山岩诗》中的“岩中清磬僧定起,洞口绿树仙家春”两句,以原拓书迹摹刻于一线天左近的一处岩壁上。虽然只有一联诗句,却刻写得惟妙惟肖,笔画瘦劲,骨力遒健,咋一看,这中宫内敛、长枪大戟的书风还真像是黄庭坚的亲笔。
老郭 摄于2023年7月
清人钱泳摹刻拓本
飞来峰下这飞来之笔,将从未践履杭州的黄庭坚书法“请”来了杭州。钱泳在落款中明言是“摹黄山谷书”,黄庭坚的名字也由此留在了西湖山水间。所以人道是龙泓洞藏着“半个”黄庭坚。这“半个”黄庭坚的背后,满满的是对于山水胜迹和名贤风骨的景仰。黄庭坚当年致敬颜真卿,致敬永州名胜,后来的钱泳又致敬黄庭坚,致敬西湖名胜,这一脉的文化滋养,大好河山方得如此多娇!
写到这里,又意外获悉:杭州孔庙竟藏着“一个”黄庭坚!赶到劳动路孔庙,在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,果见墙上嵌立一块落款为“山谷道人黄庭坚”的大字石碑,碑文为陶渊明《移居》两首诗中的第一首(昔欲居南村,非为卜其宅)。杭州孔庙1993年档案记录,此碑刻石人和年代不详,本是旧藏,新中国成立前就已“移居”孔庙了。
杭州孔庙藏
根据落款年代“建中靖国元年(1101)十二月”,可知那时黄庭坚住在荆州,第二年就因“元祐党禁”被贬谪广西宜州。又据南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记载,在前往贬所路经祁阳(今属永州)时,黄庭坚曾以草书书写陶诗四首,其中就有《移居》这首诗,并刻于当地嘉会亭侧的石壁间。胡仔喜爱黄字,曾将此摩崖石刻墨拓而归。可见黄庭坚确实写过《移居》诗。只是杭州孔庙这块碑文由楷书写成,并非胡仔所说的草书陶诗,书写时间与胡仔记载也对不上号,故而这个较完整的黄庭坚法书还是有点身世不明。
但不管怎么说,见过此碑的书法家都认准这是黄字,都说这字真好!尤其当你面对这块高147.5厘米、宽62.5厘米、厚16厘米的大碑时,当年摹刻人对于黄庭坚及其书迹的崇敬和膜拜,仿佛眼前。至于它的身世之谜,借用碑上的陶诗,我们大可以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。
宋扬庭等龙泓洞题名 局部 浙江省博物馆藏
黄庭坚的字和他老师苏轼一样,也极有个性。
苏老师喜欢找乐子,某天,瞅着黄庭坚说:“鲁直啊,你近来的字虽说很见长进,比较清劲,可有时候这笔画写得太瘦了,打个比方,就像是树梢上挂着的蛇,呵呵!”黄庭坚见老师拿自己打哈哈,也不客气,怼道:“老师您的字学生固然不敢妄议,但学生总觉着您这字扁扁矮矮的,怎么看怎么都像是石块压着的蛤蟆。”两人这么一顿互损后,哈哈大笑,还都称赏对方的批评切中了自己书法的要害。
后人归纳黄字行楷特点,“楷法妍媚,自成一家”是说字美,“以侧险为势,以横逸为功”是说笔画结构的亮点。而他自己说,当年贬谪去涪州(今重庆涪陵),舟行长江途经僰道(音bó,在今四川宜宾境内)时,观察船工荡桨击棹的娴熟身手,有所开悟而书艺长进。故而他的一撇一捺,往往有一种船桨长出、驾驭大河的气势。
尽管如此,黄庭坚却不愿人们学他的书法。他在写给友人的信《致景道十七使君》中说:
“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,虽用墨太丰,而韵有余,于今为天下第一。余书不足学,学者辄笔愞(音nuò,古同“懦”)无劲气。今乃舍子瞻而学余,未为能择术也。”拜托诸位,习字最好取法乎上,向天下第一的苏老师看齐,我这以力取胜的字没有“苏体”的韵致。
可偏偏有人就是看好他的字,譬如徽宗赵佶。这位文艺皇帝的“瘦金体”独树一帜,傲视书坛,但他对黄庭坚的字赞赏不已,也曾有过临摹。南宋状元张孝祥讲到徽宗曾评价黄庭坚字:“如抱道足学之士,坐高车驷马之上,横斜高下,无不如意。”意思说,一见黄庭坚的字,就像是看见一位饱学的守正高士,驾驭着名贵豪华的驷马大车,纵横竖直,无不随心所欲,从容自如。见字如人,学字学人,俨然将黄庭坚字视为一种榜样。可吊诡的是,也是经过这位皇帝的手笔,“高士”黄庭坚被打入了“元祐党籍”黑名单,最终客死广西宜州贬所。宋朝政治有时就是这么诡谲,这么无情。
相比之下,徽宗之子高宗赵构对黄庭坚字是打从心里喜欢,临池描摹,孜孜矻矻,学得很像样。“意造大观”特展中有一幅题作《绍兴恤刑手诏碑》的淡墨精拓,初看过去,笔势清劲,仿佛黄字。细看之下,却是赵构的笔迹:落款日期绍兴三年(1133)正月九日的“九”字上,钤盖“御书之宝”印,落款下又有“构”字变形如“伍”字的画押。赵构排行第九,画押如“伍”,这样的落款含蓄地表示了“九五之尊”的意思。
今杭州中山南路利星广场(之前为杭州卷烟厂)原是南宋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和枢密院的所在地。据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,《绍兴恤刑手诏碑》最初即刻碑立石于三省议事场所都堂之上。彼时赵构从越州返回临安城已有一年,书写此碑,是告诫典狱官员宽恤民力,敬慎刑狱。立碑都堂后,接下来就仿佛开动了印刷机,拓碑“影印”无数,从京城临安“发行”各地州县,各地再据以覆刻碑石于府衙之内。
这篇碑文通篇以黄字为榜样,亦步亦趋而成一件颁行天下的手诏,赵构的这番亲力亲为,算是对自己“偶像”的书法做了一次全国推广。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说:“高宗初作黄字,天下翕然学黄。”黄字因为赵构的推崇,一度成为大宋书法的“标杆”,虽然黄庭坚并无此愿。
京城临安的雕版印刷在两宋时期被誉为“天下第一”。但赵构似乎更青睐能够将书法原迹存真传播的碑拓技术,譬如绍兴十二年(1142)他御书上碑的《南宋石经》就是史上一项颇见规模和品质的文化工程。由他一手编撰、御书并刻碑“影印”刊行天下的黄字,也不止“恤刑诏”这一件。事实上,比“恤刑诏”还要早半年在临安刻石,并传拓各地州县的另一件黄字,影响更为深远。
观展浙江美术馆“意造大观”之前,我去了一趟临安府的衙署。
从西门清远门入临安古城,沿着临安路东行五百多米,就到了坐北朝南的临安府署。上午十点还不到,府署大门前的小广场有些空旷。趁着人少的机会,很少拍照的我给自己留了一张影。
步入府署门厅,穿过前院中一座木石结构的重檐石坊,便是府署的第二道大门——仪门(南宋时也称“正厅门”)。这是衙署内的重要大门,一般官员须在仪门前停轿下马,方可过仪门进入第二进院落,进到府署内最重要的办事场所——正厅。但是且慢,仪门和正厅之间,还有一座重要建筑要经过,这就是“公生明坊”。这是一座全石构牌坊建筑,除了四个坊柱柱头雕有传统常见的云卷纹,其他地方并无繁缛的雕花装饰,朴素无华,简洁干净,却突出了坊额上镌刻的“公生明”三个大字。
姜青青 摄
这三字又仿佛黄字。绕到石坊背后,坊额上果见有黄庭坚:“御制《戒石铭》(下钤‘临安府印’):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;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。黄庭坚。”这当然是现在仿刻的黄庭坚《戒石铭》,这“临安府”也不是南宋京城,而是元代“临安路”的属县、明代又为“临安府治”的云南建水县。
黄庭坚书《戒石铭》原文是宋太宗撰写的(原创于五代后蜀孟昶,太宗摘录而已),北宋时各地早有树碑,但仅是充作门面,故而现将摹刻的黄字拓本颁发各地,要求为官者据以刻碑,不许立在庭院中搞形式主义,必须将此作为座右铭,放在朝夕可见的办公场所内。
淳石斋藏(田振宇提供)
这件南宋重刊的《戒石铭》,我们今天还可以看见刻在湖南梧州和广西道州的两通宋碑清拓本。碑石刻制十分精美,四周饰有龙纹和灵芝瑞草纹。碑文分作上下四栏,上栏碑额篆书“太宗皇帝御制”;二栏赵构手书“御制戒石铭”之后,摹刻黄庭坚书写的十六字铭文;三栏是赵构手书诏令,一水的黄字书风;底栏则是当时宰执吕颐浩、孟庾、秦桧等人的跋文,其中有言“诏以黄庭坚所书刻之石,将以墨本赐天下”,足见南宋各地镌刻的《戒石铭》,其祖石母本皆源于杭州。南宋末年成书的《咸淳临安志》也记载了这件《戒石铭》,并称编录书中的这些官家“御制”作品,“皆杭故也”,都是杭州存有的原物。
颁布《戒石铭》后,赵构又进一步抓落实。绍兴二年十二月,差遣监察御史五人巡行各地,检查督促,若有虚与委蛇,只是将拓本墙上挂挂的,严惩不贷。这使得戒石碑很快就在南宋境内遍地开花。绍兴四年(1134)十月,宋廷议和使者魏良臣在长江北岸大仪镇(今属江苏扬州)遇见南侵的金兵。双方对谈中,金人说,他们过泗州(今江苏盱眙)一路行经各州县,多见“恤刑诏”和“戒石铭”二碑,并说:“皇帝如此爱民,煞好!”金人是否真有这般目睹和评价姑且不论,但黄字书风的“恤刑诏”和摹刻黄字的“戒石铭”在当时遍行淮河以南的宋境各州县,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
上图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藏
下图江西太和县博物馆藏
从元代直至明清,《戒石铭》一直存在于各地官署中,但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变异,如明代戒石碑正面出现黄字“公生明”,宋碑上的黄字铭文则被仿刻于碑阴,并且立碑覆亭于仪门至衙署大厅的正中甬道上。清代则或亭或坊,各地不同。雍正八年(1730)杭州府署重修正厅“苏白堂”时,仍保留了仪门至大厅甬道上的戒石亭。而云南建水现在的“临安府署”仿造的是明清时期《戒石铭》形制,建筑则是易亭为坊。
从一代书法“标杆”到千年吏治“标配”,这是黄庭坚对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。虽然这背后的推手是赵构个人对他字的喜好和推崇,但能清廉政风,利民利天下,这又何妨?
在中国传统的交友关系中,有一种叫亦师亦友的关系。苏东坡和黄山谷的关系,即可以称为亦师亦友,甚至可以叫作“半师半友半知己,半慕半尊半倾心”。如果单纯是师生关系,这种“树梢挂蛇”“与“石压蛤蟆”的互谑玩笑是开不起来的。
说到书法,颜鲁公的雄浑豪健已成为盛唐气象的典范与忠臣烈士的气格象征,自然成为后世人臣的追慕对象,苏黄也就有了共同的偶像。但是笔墨当随时代,唐人尚法,宋人尚意,苏黄也就必然会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,而二人作品所有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保留了鲁公雄强的气脉。至于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从唐太宗独好王羲之而天下皆习王字,对艺术崇尚多元审美未必是好事。
至于宋高宗赵构追慕“黄字”并号令天下刊刻《戒石铭》,虽内容正确,但形式则已束缚了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多元统一,这或许已不是黄庭坚的初衷。
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“富阳女婿”黄庭坚与杭州的关系如此。《乾隆杭州府志》说他“往还富阳,从(谢)景初学诗,竟以诗名家”,不知真假。
《咸淳临安志》载有黄山谷《钱塘旧游》诗,其中有云“南北峰岩空入梦,短长亭舍自相望”倒似有杭州影踪,也难怪南宋《舆地纪胜》、后世《全宋诗》等均沿用,但未见于黄氏文集,属孤证。
南宋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》还误将陈师道《宿钱塘尉廨》当作黄鲁直作品,以致清代杭人厉鹗《宋诗纪事》“笑纳”之,而《乾隆杭州府志》也将黄氏写宜春崇胜寺的《题竹尊者轩》错移至杭州凤凰山崇圣院名下,都是“枉费心机”,却更见杭人对这位苏门学士的心结。
“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或许唯有到“意造大观”品一品那“虽昂藏郁拔,而神闲意秾,入门自媚”的“高谢风尘之意”,才能心领神会。